风起五洲,山雨欲来
窗外的天很沉,似乎要下雨,风也吹得烈。益州虽然毗邻北边的宣州,可冬天甚少如此,大有些「风雨欲来」的意思。
窗外的天很沉,似乎要下雨,风也吹得烈。益州虽然毗邻北边的宣州,可冬天甚少如此,大有些「风雨欲来」的意思。
我坐起来,满背的黏腻,打开窗户吹风。
自打十岁那年,郢都破了,我夜里就时常做梦。梦里有时是逃亡,有时是断肢,总之漫天的红色,都是人血。
有的时候,我也会觉得梦里隐约有人在唤我,但一醒来脑袋就全都空了,根本想不起来梦里到底有什么,只记得睡梦中曾一片繁杂。
我们大业薛氏,现在虽仍保留郢都,保留皇宫,可八年前开始的那场十六州混战,把大业弄得四分五裂。困守益州以后,宫里就养不起那么多人了,公主们的身边几乎没人伺候。
无事可做,我撑着头窝在椅子里发呆。
「公主,四州共同进犯,陛下要将您送给宣州蛮子,换取宣州铁骑!」莹雪提着裙摆,匆匆赶来找到我,人还没到,就听见她的脚步声了。这要换做以前,是不许的,宫里禁止疾行,行止求静。
「嗯… 知道了。」前几天莹雪跑来告诉我,宣州意图不轨,想踏平益州的时候,我就猜到我可能终于要被送人。可后来四州都有异动,我就不确定会被送去哪儿:
是宣州的萧蒙,端州的钱坤,济州的周不语,还是凉州的石宜?
原来最终还是要送去宣州… 哎,若能送去济州是最好的,周不语好歹是个文人。读书人总还是有些许读书人的清高,待我可能会有礼一些。
「谢谢你,莹雪。」莹雪曾是我身边的贴身宫女,跟了我许多年。大业败落,我那个父皇一路出逃,后来被各州的王重新「请」回皇宫以后,宫里的人就重新编了。
莹雪被重新编进了明华堂,那是早朝的地方。
当然,送她进明华堂,我是废了大力气的,因为就算命运不能为我左右,我也不想缩在后宫里,做一个耳聋目盲的人。死也要死个明白吧!
「只有你还真正把我当成主子。」如今淳帝的女儿,都只是货品。
八年前,大业分崩离析,历经五年混战,礼乐崩坏,如今五州鼎立,相互制衡的局面已然形成。
可益州弱得很,没什么话语权,这么些年一直被打来打去,所以这东明大陆,本质上是四州鼎立。那益州凭什么还能存在?
凭的是这片大陆上的人对正统的执念啊——薛氏统治这里很多年了,具体有多少年,我不清楚,但我知道大业的历史很长,长到半个藏书阁里的书,都与之有关。
除了瀚北萧家,他们没有这个观念。
八年前混战的时候,萧蒙也才堪堪十五,他随其父亲喊过话:皇帝轮流做,今年到我家!就是这句话,吓得我那没用的父皇屁滚尿流。
「公主你可知,陛下今日坐在大殿上,听到宣州萧蒙拜见,说要借他骑兵时,脸都气绿了,忍不住就大骂萧蒙是个狼崽子!」莹雪皱着眉,蹲跪在我脚边,忧心忡忡地拉住我的手腕,「陛下说挑起战事的是宣州,如今说要借我们骑兵的,还是宣州。」
是啊,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,萧蒙到底想要什么呢?
手腕翻转,我挣开莹雪的手:「去吧,回明华堂去。当心被人发现你偷溜出来,是要受罚的。」
我此刻只想一个人静静。
我父皇,淳帝,之所以还能够在益州逍遥快活,光靠着大家对正统血脉的迷信可不够,那只能愚弄百姓。真正身居高位的人,比如各州的王,心里都明白,只要彻底颠覆了薛氏,假以时日,他就能成为新的正统。
所以我父皇虽无能,可心狠。
淳帝的儿女不值钱,阖宫上下谁不知道。尤其是女儿,连名字都没有,只按行序来叫。自打郢都破了,淳帝就开始把不中用的儿子推出去给人杀,杀完大办一场丧事,又或者把女儿送人。
送出去的女儿没一个落得好下场的,比直接推出去送命的儿子还惨。
我行十三,兄长和姐姐们叫我小十三,父皇在朝堂上叫我十三,底下的「臣子们」叫我十三公主。
可我没有再没有兄长了,他们被父皇推出去,杀了个干净。我也没有姐姐了,她们都被送出去,或是笼络下臣,或是寻求庇护。
总之,宫里现在就剩下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。
只正经当了十年公主,而后这八年,若不是我生得明艳动人,被逃亡路上的父皇当胸一脚,疼得眉头直皱,他发现我比其他姐妹都好看,想把我用在刀刃上,我恐怕早就和那些个姐姐一样,被草草送人,又草草退回,循环往复,直到疯疯癫癫。又或者被折磨得断手断脚,死状凄惨…
一想到这里,我就胃里翻涌,手指也不自觉地颤抖得厉害。
我闭上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可耳边仿佛能够听到横天阙边,端州大军的喊杀声。我静不下来。
横天阙是益州与端州之间唯一一道天险屏障,渡过横天阙,便是坦途,若没有铁骑相助,端州大军便可长驱直入进益州。
而益州,真的没有铁骑。
且不谈骑兵,益州甚至没有一支拿得出手的军队,连凉州都比不上。
石宜虽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商贾出身,可商人也有商人的好,凉州富得流油。他们有的是钱,能够把军队养得兵肥马壮。
宣州有铁骑,不仅如此,他们还主动上门来,要给我们铁骑。可就算挡住了西边的端州,南边的凉、济二州呢?他们不也有动作吗?
我一个被豢养的笼中鸟,着实摸不透外面的风云。
「十三公主!」门口响起太监独有的尖细嗓音,「咱家来给公主报个喜,陛下已为公主觅得良人,今夜就能嫁过去。」
呵,真是讽刺。公主分明是被送人,却要说是嫁人,按照他们这「喜庆」的说法,大姐姐被一次「嫁」给十个人,倒是她的福分了?
「窦公公…」我唤他一声,恭敬地见了礼。这人是父皇身边的大太监,前朝后宫里许多事,都要经他的手过。
大业崩裂前就是这样,朝堂上已无可用之人:宦官当道,丞相死谏,将军寒心。
我想过他们的手脚会很快,却没想到会这么快,如此迫不及待…
他带来的衣服很薄,是瀚北女人的制式,穿上之后会漏着腰。这大冬天的,我真怕自己会被冻坏。
可现下我更怕的,是眼前的窦公公,窦还恩。
屋子很小很小,是从前宫女们住的地方,可如今公主们也住这样的地方了。没有里间、外间之分,床榻、桌子一览无遗。我就在窦还恩面前,背过身去,把衣服一件一件褪下来。
窦还恩的手顺着我赤裸的脊背划了两下,多年前被皮鞭抽烂过的后背狠狠收缩。
那只保养细腻的手在我身上打了几圈转,最终选择停留在我的唇边。
还是那个夜晚,被鞭柄撕裂过的唇角,又开始火辣辣得疼。
「皓腕凝霜雪,十三公主这手腕也生的好看,不比这张脸逊色。」窦还恩放过我的嘴唇,猛地拉起我的手腕。
背着身子,我强忍住把手抽出来的欲望,一动不动地任由他拽着。
「公公谬赞。」等到他终于松手,我飞快地套上那套瀚北服饰,双手掩着露出来的腰,低眉顺目地立在一旁。
他喜欢我的手腕,可八年前的那个夜晚,他捆着我的手腕,捆到最后,手指发紫,手腕上留了发黑的勒痕。他差点把我这双手废了去。
窦还恩这样的恶人,活剐三千刀尚不能平愤。
身上这些不堪的痕迹,用了近一年才养好,现在已了无痕迹。可留在我心里的痕迹呢?我是一辈子都要记着的。
这便是我为把莹雪塞进明华堂而付出的代价。
我找了个自以为巧妙的借口,说明华堂在他窦公公的眼皮子底下,最是安稳,莹雪跟我多年,我舍不得她去做粗使宫女。
可窦还恩说:郢都哪个角落,不在他眼皮子底下?
抬眼看见窦还恩一脸的回味,我恶心得要吐,也害怕得想哭——我虽还是完璧之身,可我倒宁愿用这完璧之身,免去那雪夜里残忍的折磨。
乱世里,皇亲贵胄不值钱,人命不值钱,女儿家的贞洁又能值几个钱?
「走吧,去离院候着,今晚荣宝殿,陛下要宴贵客。」贵客就是宣州来的萧蒙。
披着银白色的狐裘,手里还抱着一只汤婆子,可我仍旧在今年格外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他们给我备的这身衣服,是夏衫。
「冷?」窦还恩回过头,难得好心地问我。
我点点头,又拢了拢身上的狐裘,希望他能听见我的心声,给我换一件厚实的衣服,哪怕是秋装也好。
「那便祈祷时间过得快些,芙蓉帐暖度春宵,到时候就不冷了。」说完,窦还恩阴测测地笑了。
我抱着汤婆子,哆嗦得更厉害了,上下牙极快地磕在一起,发出细细绵绵的哒哒声。
窦还恩看着我的反应,从鼻子里哼出一声,满意地继续领着我往离院去。
离院的正殿里烧着地龙,甫一进殿,我就松了眉头。终究是不敢把我冻坏了,今晚能不能顺利拿到宣州铁骑,叫益州少挨些打,还指着我这副身子呢。
差了个宫女进来陪着我,正殿的门被从外锁上,殿内只留了一扇窗子通风透气,可窗边也是有人把手的。
那宫女哪里都好,叫她捏腿就捏腿,叫她捶肩就捶肩,可她膀大腰圆,看得我委实有些害怕。
但凡我想使什么花花肠子,这位姐姐肯定会拧断我的胳膊。所以我老老实实,不耍花招。
不是我不想,是任何小花招,都没有用,我就是淳帝为此刻准备的,逃不开,避不过,这便是大业薛氏十三公主的宿命。
在离院被关到傍晚。
日头还没完全沉下去,我歪在正殿的罗汉床上,透过唯一一扇打开的窗户,看铺满窗沿边那方天空的红霞。
看起来真暖啊… 眯着眼,我伸手虚握一把。
「十三公主。」随着门口锁链碰撞的几声脆响,窦还恩尖细中带着两分沙哑的独特嗓音戳进我的耳朵,刺得我一哆嗦。
「窦公公。」我忙起身穿鞋,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局促,把不安和惧怕都摆在脸上。
门口立着的人身着石青色四爪蟒纹袍,八条蟒绣工极佳,一看就是御赐的好东西。这是文武四至六品官的制式,一个都领侍,四品,窦还恩今日还不算逾矩。
他身后的随侍小心翼翼地为他打着灯,衬得我这「正头主子」更加没有气势。盯着窦还恩的身形轮廓,我是大气也不敢喘。
「宣州那边的的贵客到了,」窦还恩摆摆手,让左右的人退下去,缓缓向我靠近两步,「其中有个叫景和的幕僚,很年轻,不是瀚北人,可深得萧蒙信任,你去,探探他。」
「窦公公,我…」
「还要咱家教你?你们个个都是好好调教过的,关于如何拿到有用的东西,想必不用咱家再多说吧?」
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——明面上是把我送给萧蒙,可背地里也要我勾着那个幕僚。曾经大业的公主,如今同勾栏里的妓子没什么分别,甚至还不如她们。
窦还恩绕着我,缓缓踱了一圈:「十三你最是天赋异禀,八年前我都还没来得及教,你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」
我站着没动,眼皮跳了跳。
被领进荣宝殿的时候,我觉得暖和,可等宴会上众人酒过三巡,我褪了狐裘,沿途的目光剐得我腰间的皮肤生疼,荣宝殿大开的漆门处吹进来的风刮得我脑袋昏沉。
跪在荣宝殿主座下方,我抬头瞟了一眼正前方喝得东倒西歪的淳帝,还有立在他身旁的窦还恩,同时余光瞥见淳帝右手边坐着的萧蒙。
我没见过萧蒙,可我猜得到哪个是他——古铜色的健康肤色、大马金刀的坐姿和这顶顶尊贵的座位顺序,无不在告诉我,这是宣州来的那位贵客。
与他正对着的,是左边的贺丞相,贺今朝。他是先丞相贺梁的儿子。
贺梁是个好丞相,在郢都城破的前两年,血溅朝堂,死谏淳帝收拢宦官的权柄。可贺梁白死了,他的儿子同窦还恩背地里有了勾当,贺今朝一上来就把他老爹的心血全都糟践了。
「这是朕最疼爱的一个女儿,小十三… 嗝…」我那个没用的父皇坐在上首,醉醺醺地开口,还打了个酒嗝。
哎… 大业早就不在了,还自称什么「朕」?各州给些面子,还真就顺杆爬了?
我安安静静地跪着,被他们当成货品交易,斜后方两道直勾勾的目光打量着我,叫我浑身不自在。
在我被又一阵凉风吹得抖了一下的时候,身上忽然罩下来一件带着体温的大氅。
愕然侧头,见到旁边站着一面目清俊的青衣公子。这模样瞧着不像是瀚北那些粗野的汉子,倒像是曾经郢都里,哪个世家大族的贵公子,俊雅无双。
一刹那,熟悉感涌上心头。青衫烟雨客,似是故人来。
这个人就这么静静地望着我,我从没见过他,可莫名心安。
「景和,何故如此?」萧蒙抢在淳帝之前问了话。
「殿下,十三公主… 貌似故人…」我身侧的青衣公子拜了一拜,恭敬地答话。
荣宝殿里霎时沉静,没有人知道他这句话要如何接。
我慌了,想要辩解,可无从开口,因为他只说我貌似故人,却没说我就是故人。我若反驳,倒显得我同他真有什么了。
「景公子的故人,可是与十三公主一般姝艳无双?」贺今朝端着酒杯,笑着开口。
景和又是恭敬一拜,面上是不变的严肃认真:「正是。娇艳明媚、灵巧婉约,一般无二。」
我怔住了,不觉得自己与他嘴里这个需集万千宠爱才能养出来的娇俏女子,有什么关系。等我回过神,只听得萧蒙说:
「你从不曾如此失态。」
萧蒙松了口,我被他宠信的这个,叫做景和的幕僚给要了去。
也算是殊途同归吧,窦还恩不正希望我能去这个景和身边么?这下可正正好了,人家对我有兴趣呢。
益州的冬天虽一贯温和,可终究是不能不穿氅衣的。
随着景和步行在宫道里,我看着他单薄的背影几次欲言又止,终是忍不住叫了他一声。
「大人…」不确定要怎么称呼他。
除了益州,其余四州没有严谨的官僚体系。虽然益州现下也是上下一团乱麻,可那些祖制的壳子还在。
「大人,夜里风大,仔细身子。」说着我就要去解那件氅衣。
「你且穿着,」景和隔着衣袖按住我的手,「你今晚穿得单薄。」
脸腾得就红了:是了,我自己里头穿得更少,如果脱了大氅,决计是要冻病的。可马车只在宫门外候着,离这儿约摸还要走近一刻。
若不是这人走得仓促又一脸不容反驳,我本可以去拿那件狐裘的。
「可是大人,这儿里宫门还有些远,这么冻着,怕是不好…」我的本意是差人回去取那件狐裘。
谁知景和一把横抱起我:「如此,就这么走吧。」
把脸悄悄埋进衣领,挡住了自己惊诧的神色。看着这人正经的表情,我很难觉得他有什么歪心思。
方才还觉得他身子单薄,怕是抱不动我,可直到出了宫门,上了他的车驾,我才发觉他的怀抱竟是这么结实,再次让我心安,隐隐又叫我有些贪恋。
这车驾造价不菲。底下有处空箱,冬天可烧炭,夏天可存冰,都是能工巧匠寻了好料子打的。
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好料子,和什么样的手巧匠人。从前只在书里头读过,却没亲眼见过,如今是头一遭。
马车摇晃,我俩对坐无语。
就在我垂着眼要睡着的时候,忽然听到他问我:「你叫什么?」
我心里一愣,来不及纠结他不称我公主,毕竟我算不上什么公主了。开口就答:「十三。」
「这是行序,没有正经名字?」他显然是不信,觉得我在敷衍他。
「大人,大家确实是这么叫我的…」
景和陷入了沉默。
直到马车停下,我发现他带我到了宣州骑兵的军营里,这人都没再开口。
我摸不透他的心思,心里慌极了,咬了咬嘴唇,盯着他看,却不出声。
良久,他安顿我到他的帐子:「军营不比别处,你且将就些时日,我睡案边就好。」
景和指了指靠近门口的一张小几,又拖了屏风过来,隔在床与小几之间。临到转身要走,他状似极不经意地问:
「可愿随我姓景?」
他皱了皱眉,「不姓薛了,随我姓景,就叫景妍。」
我又呆住。这人从出现开始,就一直出乎我的意料,总是猝不及防地敲打着我心底的柔软。
「愿意,愿意的大人,景妍愿意。」我露出欣喜的笑,就要跪他——他给我赐名,我便是他的从属了。
景和虚扶住我,眼神有些游离,点了点头就去了屏风另一头。
我忐忑地和衣而卧。他的帐子里暖融融的,我的脑袋又昏沉起来,很快就睡着了。
又是梦里,断肢、肉泥、马车、残月… 铺天盖地的红浪朝我卷来,打得我茫然无措。然后又是一顿嘈杂,是什么声音…?
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… 是我?都是我?
「景妍,醒醒。」景和打着灯,蹲在我的床头,见我醒来就松开了我的手:「可是魇着了?」
「大人…」我神情呆滞,似乎还困在梦里。
「梦里有什么?」他一副好耐心的模样。
「记不得了大人,醒来就记不得了…」我似喃喃自语,眼睛依旧空洞地睁着,手指主动攀上他的衣袖。
他叹口气,顿了顿,又问:「可曾读过书?」
「许久以前曾读过一些。」不知道他要做什么,我只能老实回答。
「往后就还跟着我读书吧,不必叫我大人。」
我看着他,那张脸在灯影里朦胧起来,叫我越发觉得熟悉。
「先生…?」我试探着改了口,见他垂眸沉思了一会儿,没有反驳,我又大着胆子叫了一声。
他没应,起身往外走,我翻身下床,跪在地上,一把牵住他的衣摆:「先生救我脱苦海,景妍愿做先生手里的刀刃。」
不知道他在谋求什么,但我觉得我对他定然有用,不然枉费他在荣宝殿顶着风头要下我。
与其被窦还恩要挟着,倒不如「投了敌」。我下意识觉得跟着他混,我或许还有出头之日。总之走一步看一步,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些。
「起来,不要你做刀刃。」景和握着我的肩,不重,却很坚定。
「睡吧。」最后撂下两个字,他没再看我。侧身越过屏风时,我看到了他眼里映着的火苗。
次日醒来,床头放了一套益州女子的常服。不是宫里头贵人们常穿的绫罗绸缎,也不至于是粗布麻衣,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料子,摸在手里细细的,很舒服。
卸下手腕上叮叮当当的一大串,又脱了昨晚瀚北女人的夏衫,钻进景和留在这里的衣裙,我浑身都自在起来。
绕过屏风,案边早就空了,我并不知晓他去了哪里。
在原地站了一会儿,撩开帘子出去。门口左右两边分别立着一名少年和一名少女,他们俩见我出来,齐齐向我行礼:
「夫人,今早窦公公来了,公子已经去了。」
「夫人」二字惊得我往后退了一步,连忙摆手:「不不,我不是什么夫人…」我只是个礼品罢了。
那二人相互对望一眼,少年开口:「我叫叶里,她叫花间。」
少年指了指身旁的少女,「公子吩咐,今日起我们兄妹随侍姑娘左右。」
我默了一会儿,点点头,「先生有心了,那便有劳二位。」
很久没有被人这么周到地照顾过了。来这儿之前,我都是自己打水梳洗,偶尔还要照顾年纪小的弟弟妹妹。
「叶里花间,真好听。一听便晓得是一家人。」我看着镜子里少女的面容,觉得她和她哥哥都不像是瀚北出身。斟酌半天,尝试着开口搭话。
「是公子取的名字。」花间手指翻飞,替我挽了一个端庄淑雅的发髻,「我和哥哥都是公子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。」
竟是… 如此吗… 受过景和这般恩惠,这二人当是他的心腹了吧。
两人年纪都不算大,可行事沉稳,想来定然有什么过人之处,景和应当把他们教得很好。
「今日这发髻…」我摸了摸簪在一旁的石榴钗。
「姑娘,且随我去见公子和窦公公吧。」花间冲我笑笑,扶我起来,提我系上氅衣,领着我往外走。
哦,我忘了,窦还恩来了,我是要去见见他的。这发髻是应当端庄正式些。
走在路上,我第一次知道军营的模样。沿路都有威风凛凛的瀚北军士巡逻,我看着,莫名就有安全感,仿佛行走在他们中间,没有人能伤得了我。
不知走了多久,我到了一个白色的帐子前,叶里和花间停下脚步,示意我进去。
这军营里的帐子都长一个模样,连景和住的也是这样白白的一只,我根本就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区别。
萧蒙不在,窦还恩同景和对坐在帐内。见我进来,窦还恩难得地起身向我行礼:「十三公主。」
我一时不适应,站在门口有些别扭。
景和过来牵住我的手,拉着我坐到他身旁,继续同窦还恩寒暄。
指了指一旁的箱子,景和面带笑意地望向我:「窦公公今日送来的,你去看看,喜不喜欢。」
我在窦还恩毒蛇般的目光注视下,缓缓打开了那只箱子。
没什么新鲜,不过是些珠宝首饰和衣服,只不过都是按照正经公主制式来的,比我先前在宫里用的要好上许多。
「这些东西,公主可还喜欢?」又是那尖细又沙哑的声音,我手臂上的鸡皮疙瘩爬了起来。
「喜… 喜欢。窦公公有心了。」我没有抬头,背对着窦还恩,「不知宫里父皇可还安好?」
窦还恩答「安好」。
我又问弟弟妹妹们有没有不乖。
窦还恩又答「乖顺」。
来来去去,我们之间总离不开宫里那几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景和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,意思仿佛是让我们放开了聊,不必束手束脚。
「十三,这景公子对你很是看重啊…」见景和出去,窦还恩又贴近了我才说话。
「窦公公… 我,我们昨晚什么也没发生。」在他不怀好意的打量下,我什么都招了。
「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吗?」窦还恩转了转手上的扳指,他每次起坏心思的时候,都会这么做,「在宣州要借给我们的三千铁骑营里。」
「我知道你好奇萧蒙为何不在。他回宣州大军的军营了。大军两日后开拔,借道益州,直奔凉、济二州的交汇处。」
听到这里我好像隐约猜到宣州的意图了,也大概能知道窦还恩此行是要我做什么。
「两日,你想办法把景和留在这里,不要让他跟着萧蒙。」
短短两日,我与景和素昧平生,他凭什么就会被我留在益州?
萧蒙倚重他,所以他绝非耽于女色的泛泛之辈。窦还恩这是在为难我。
「窦公公,景公子他怕是不会为我所困。」
「没让你用美色困住他,只是让他在益州多耽搁几日,赶不上大军开拔罢了。」窦还恩啧了一声,仿佛在嘲讽我的愚笨。
我怯怯地看着他,唯唯诺诺的模样又引得他面上一阵不耐。
「没用的东西。」他啐道,「生母下贱,白生了一副好皮囊。」
他不提我都要忘了自己的生母,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洒扫宫女。因有几分姿色,得了醉酒淳帝的临幸。
我这副容貌,不像我的生母,也不像淳帝。若非生母身世清白,淳帝幸过以后,有专人看管,否则任谁都不会觉得我是淳帝的孩子。
「全凭公公吩咐。」我放低了姿态,语气里尽是讨好,仿佛生怕遭了他厌弃。
窦还恩依旧转着那只翡翠玉扳指,不知是想到了什么,脸色忽然好起来:「十三,倘若景和真是个正人君子,你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贞洁,不到万不得已,不可交予他。」
「是。」我没有一丁点贵胄的骄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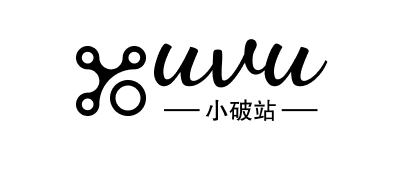
评论(0)